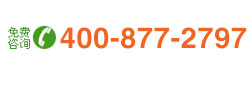吉庆街的“四大天王”
很不巧,我们到达吉庆街的时候,麻雀已经回去了,老通城因为身体不适没来,“四大天王”在场的只有黄瓜和拉兹。拉兹戴着一顶黑色牛仔帽,上面赫然入目印着“四大天王 拉兹”的字样。他背着手风琴,缀着闪闪发光的耳垂,在客人群里穿梭弹唱,谈笑自如。
武汉吉庆街,长170余米,宽9米。两旁的人行道,若是清晨时分看来,是一条标准的两车道,容得下两辆卡车并行;而在夜晚时分看来,则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市场,人行道上摆满餐桌,客人纷纷就座,身着唐装旗袍的服务员喜迎来客。即使桌与桌之间的空隙,也被卖花姑娘、擦鞋工和艺人们占满。
人不分南北,客不论东西,在吉庆街,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,也不会有人停下手中的杯筷来观望,一切都再平常不过,“陶红拍《来来往往》时到这里体验生活,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”。左边的一桌是一群老外,他们拿筷子的姿势一点都不笨拙;右边是北京来的客人,据说,他们经常在周末打个“飞的”跑来武汉,住五星级酒店,然后只为到吉庆街宵夜;前面,是本地的一家人,大人带着小孩,妻子一边给孩子喂食一边抱怨太吵闹。
若是不吵闹,又怎么叫吉庆街。入口处的一副对联上写着:“吉云照影觥樽尽显生活秀,庆雨映灯弦歌舒展岁月稠。”稠长的岁月里,觥樽交杯间,弦歌之声中灯笼映照着每个来客的脸,生活秀,多么贴切的形容。

这里的吃食并没有什么特别,换句话说,这里能吃到的,别的地方都能吃到。但是这里能看到,能享受到的,别的地方却没有。从每天下午五点开始,到次日凌晨,吉庆街上演着一幕幕交响曲,京剧、黄梅戏、湖北大鼓、二人转;琵琶、二胡、萨克斯、葫芦丝;通俗、民歌、摇滚、歌剧……无论是离我们生活很远濒临灭绝的剧种,还是唱臭大街的《两只蝴蝶》和《冲动的惩罚》,在这里,你只须花到十块钱,就能听到字正腔圆的演绎,用一位艺人的话来说,“你买张正版CD还要好几十块”。
单曲10元,乐队合唱30元,漫画20元,素描40元,“单个娱乐项目不超过50元”,这就是吉庆街的消费标准。当然,你还可以还价,“十块钱三首,唱不?”假装犹豫片刻,然后爽快地成交,三首唱毕,十块,走人。也有不肯减价的,“老板,我唱不好,你叫声停,你一分钱不把我走人。我唱得好,老板你就多赏点。”把气一沉,嗓音一开,丰富的表情,不输于舞台上的歌星。“歌星还有假唱的嘛,我们吉庆街没有。”多半,艺人唱得如痴如醉,客人听得心花怒放。
时光倒退二十年,这里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排档口。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开始有艺人来这里献唱,伴随着擦鞋工、卖花姑娘和琴童的进驻,吉庆街逐渐形成了规模。人多的地方,势必混乱,酗酒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。政府几度取缔,然而吉庆街就像顽强的小草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武汉本土作家池莉在小说中写道,吉庆街每取缔一回,其实是无形中为其做了一次广告。政府意识到堵不如疏,于是在2001年介入管理,并进行整顿清理,所有艺人经考核后持证上岗,并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。
吉庆街的艺人,也是分实力派和偶像派的。最早,这里是江湖艺人的天下,吹拉弹唱无所不包。很多擦鞋工看着唱歌好挣钱,于是纷纷放下鞋架,买一把吉它或者二胡,找个老师练练嗓子,一两个月后再出现时,已经俨然是“艺人”派头,哪怕还只会弹一个和弦,有的甚至连音都从来没调准过。当然,吉它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件饰物,客人们需要的,也无非是即买即得的快意体验。唱上一段时间,感觉唱歌太辛苦,而且毕竟是“速成班”的,既不叫好也不叫座,还是干回老本行,接着擦皮鞋好了。也有赶时髦的,从“艺人”摇身一变成为“摄影师”,拿着一部相机,“照相容易学嘛,只要会按快门,赚得不多,不过不辛苦。”

吉庆街的名气越来越大,客人越来越多,艺人们的“出场费”也逐渐有了高低之分。为了能拿到更高的“出场费”,开始有人以“天王”自诩,一时间,吉庆街遍地是天王,客人饱受伪劣“天王”之苦。在艺人们的自发组织下,吉庆街评选出了公认的“四大天王”:麻雀、老通城、拉兹、黄瓜。
四人各具特色,名气最大的当属麻雀,在很多人眼里,他已经成了吉庆街的代名词。“他可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,雪村的专辑开发布公,专门请麻雀去参加,负责来回的机票,还当面夸他,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。”麻雀90年代从安徽来到武汉讨生活,起初不知遭过多少白眼,终于凭着实力,在吉庆街站稳了脚。接着从安徽拉了很多同乡过来,并形成了今天吉庆街阵容庞大的“安徽帮”。
吉庆街的艺人,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王凡留着一头长发,看上去,像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“摇滚青年”,他说他已经年过30了。30岁的王凡16岁辍学出外打工,后来迷上了画画,于是四处访师学艺。挣了点钱后,王凡回家读书并考上了大学,“一支笔,几张纸,晚上就在吉庆街画画,客人要什么就画什么,大学几年的学费都是这样赚来的。”大学毕业后,王凡背上画板,绕着中国转了个圈,“一般人去旅游要考虑很多问题,对我来说,只要有纸和笔就够了,走到哪画到哪,挣够了路费再赶往下一个地方。”走遍了中国的王凡,还是回到了吉庆街,“不管走到哪里,我还是会怀念吉庆街,客人也好,(餐厅)老板也好,一想到他们就觉得亲切。这么说吧,我像一条鱼,吉庆街像池塘,我没办法离开他了。”
杨阳,中国汪派琵琶第三代嫡传弟子,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会员,厚厚的镜片里透出睿智的光芒。常年的吉庆街生活,并没有改变他身上高贵的音乐家气质。本可颐养天年的杨阳,因为儿子在乌克兰学习钢琴需要巨额学费,于是和几个老伙计组成一个乐队,来吉庆街献艺。曾经的社会名流,而今整日与江湖艺人为伍,并面对客人的挑剔和责难,最初多少有些难为情。“我在这里经常碰到我以前的学生,他们有些很不能理解,觉得我这个老师给他丢了脸。有个学生,有次见到了我,转过头去装作不认识,我以前教他时,经常单独给他开小灶,没想到现在他这样对我啊。”近而近之,杨阳也就豁达了,开始坦然面对这一切,偶尔和客人聊聊天,不再躲闪媒体的采访,“有个学生,带着他的朋友来这里吃饭,看到了我,拉我过去向朋友介绍我,并紧紧握住我的手说,杨老师,你要保重身体啊。”说到这里,杨阳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,摘下眼镜来擦了擦眼角。
客人与客人间细小的夹缝,对艺人们而言,是一个个巨大的空间,意味着即将上演的一出喜剧或悲剧,和金钱。刘喜年,《武汉晨报》的漫画作者,对吉庆街的过去和现在了如指掌,“我为什么喜欢这里?因为好挣钱啊。漫画好画,客人要的也就是个快餐式的体验。” 刘喜年拿来一副扑克和一张《怎能孤芳自赏》碟片,“每张扑克牌上是一个艺人的漫画,碟里收录了吉庆街的经典歌曲,看完后你会更加了解这条街。”
夜色逐渐朦胧,抬眼望去,悬挂着空中的灯笼映照着远处楼房上雕花的栏杆。有人大声划拳,有人浅笑低语,恣意或者狂荡,皆淹没在酒香和喧闹中。手翘兰花指的“潇洒”,声悲泣下的彩虹妹妹,素衣长裙两条辫梢垂在胸口的卖花女,手持黄瓜让人猜不准性别的“黄瓜”,背着吉它在阴暗的角落里小憩的姑娘……这里没有舞台,这里是展现世间百态最大的舞台;这里没有笑声,这里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;这里没有黑夜,这里的一切没有一样看得清楚;这里没有聚散离别,天下熙攘,我们来过,旋即离去。